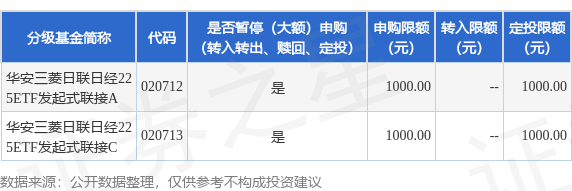作者:吴树鸣
岁月悠悠,随风而去,飘不去的是我童年、少年生命中的记忆,它绘成了我儿时五彩缤纷的风景。童年的榆树铃、碾盘石和清澈河水,那些同甘共苦的日子虽已远去,老庄的情景总会浮现眼前盟牛配资,教我以诚待人,给我力量,在人生无数个彷徨之日,却化作人生路上义无反顾的力量。
屈指算来,从老庄举村北迁,也已13个年头了。那老庄凹字形的庄子面向正东,正陷在三面环崖,一面对河的地方。一条通向别村的南北过境大路从河东边伸过来,檫过村子东边向西北延伸而去,从这条路中间开始斜向西南方向岔口伸出了一条进村路,在距岔路交叉处十丈左右,路边三尺高的土台上,有一棵盆口粗、三丈多高的大榆树。榆树在一丈五尺高的地方猛的一弯折向天空,就在这弯脖处,不知什么时候就拴着一听古老的生铁挂钟,钟的中间晃动着的铁棒头,穿着一根麻绳,一直垂到下面大人举手够得着的地方。从我懂事起,就知道从这里时常发出“铛——、铛——、铛——”沉长而幽闷的铃声。它号令着这个清末民初的老庄,号令着几百号人闻铃声起舞。在这棵愉树铃下向南六、七尺处,靠着通向村子的大路边,斜躺着一个八尺见方的大石头,人称碾盘石,石顶已磨得乌黑发亮,碾盘石的周围有几个大小不等的“卫石”,在它们的周围,一圈有五、六个大柿树,反正从我记事起,就知道柿树是这么大,一个树到秋天能摘一大麻袋黄橙橙的柿子。在柿子树东面、穿过一大片槐树林向东200米,就是一条各色顽石铺就的、清澈的浅河水,它是全村老少四季洗衣、夏季洗澡的天然盆池,也是全村盖房建屋取水的自然资源,也是我们这些淘气孩子夏季嘻嘻打闹的避暑地。在榆树正西约500米处、二丈多高的土崖下,在我家窑洞南墙外有个大石头碾盘,碾盘上有一个井口那么大的石碌碌、石碌碌中间有个洞,一根七、八尺长的大木头,从石碌碌轴心穿了过去,大木头的一头固定在碾盘的中间,人们便推着它转圈碾压辣椒,谷子,或者给驴蒙上眼睛,任其绕着碾盘转圈……
展开剩余49%磕盘的紧东面有两棵我家的枣树、还有一棵好几丈高的大桑树,听父亲说盟牛配资,那些树比我们年龄大几倍。再向南50米在村上草棚会议室后面,有一棵一围大的枸树,人们常常上去摘枸树叶子喂猪。在它下面不远,有一凑野蔷薇,逢到春夏花开一大片,持续很久很久,庄子最南头被人称作二爷二婆的人家院子中,有满院的葡萄架。最令村人欣慰的是南头那优于周围几个村子的吃水古井,每逢干旱也不干枯。整个庄子虽参差不齐、倒也绿树摭荫、古道环绕,颇有几份田园景观。有的是宁静、恬淡、肃穆。
小的时候,初春和伙伴们光着脚丫上榆树采那累累的榆钱,或者在河边采那嫩香诱人的的槐花,拿回家母亲会蒸出香喷喷的榆钱、或者槐花麦饭;夏天我们会背着大人偷偷地去河里“扑嗵”,晚上则围在大石上或碾盘周围,听大人们讲故事、或者海阔天空地谝他们当年的那些“五马长缰绳”的轶闻;深秋,用长杆网圈套柿树上红彤彤的软柿子,而后围在大石头,或者展盘上“平均分配”。当串串珍珠似的葡萄熟透时,那被称作“二爷”“二婆”的老人便会家家奉送一点,请“他叔、他姨、娃娃们”都“尝尝”;冬天则是在那大榆树下,聚来伙伴、排“队伍”,捉迷藏,学“样板戏”,或者面向哗哗的浅河水引喉高歌,有时也在古井边帮老爷爷老婆婆抬水换“好吃的”。
那时,村子普遍口粮紧,十有七、八家吃的接济不上。穷虽穷,庄户邻里倒也东拼西凑,同甘共苦,互助互爱。听说最初老庄只有三、五户人家,也都是这样过来的。那时,每每见慈祥、和善的母亲,拉着邻人“娃他姨、娃他嫂”捐助的手,千恩万谢的情景,幼小的我心里虽然酸楚难耐,但仍悄悄咬紧牙关,决心有朝一日回报这悠悠深切的乡亲。
沦海桑田,世事更迭。随着老庄的迁移,村容整齐了,人们日子也一天天如芝麻开花一节节高,人人精神饱满,红光满面,昔日生活窘迫的愁容消失了。同时似乎也消失了老庄的古风、消失了老庄浓郁的乡情味、和那淳朴的民风民俗。每每想起早已变成耕地的老庄,我怅然若失,一种难以名状的情结重重地压抑在心头,那对老庄的眷恋之情便油然滋生开来……
1996年10月31夜于周至
发布于:陕西省富灯网提示:文章来自网络,不代表本站观点。